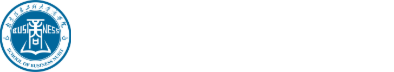卷首语
“革命者光明磊落、视死如归,只有站着死,绝不跪下!”
——陈延年

背景简介
1927年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爆发后,中共中央于危局中紧急巩固上海革命中枢。国共合作破裂的腥风血雨里,兼具军事谋略与国际视野的特派力量迅速集结,依托江浙皖三省的革命脉络,在思想启蒙与斗争实践中继续奋斗。这座自1921年建党之初便担起南北呼应的红色堡垒,既有《国际歌》译介激荡的思想觉醒,亦存五卅怒潮锻造的工人铁军,更凝结着先进青年革命的星火传承。上海党组织以工人抗争为轴心,保存火种、积蓄力量,为日后革命浪潮的再度奔涌埋下伏笔。
布衣挽车,赤心破障。沪粤烽烟里,青年先锋褪去长衫执车辕,于壁垒中叩开工农大门。陈延年以躬身之姿诠释劳工神圣,在港报讥讽声里高扬信仰旌旗。省港罢工十六月的炽焰,熔铸出国际工运史的东方丰碑;五千工农入党的星火,照亮珠江畔的觉醒长夜。携卷跨洋的陈氏兄弟踏浪西行,在颠簸邮轮上批注代表新思想的典籍,而他们早已将“舍身许国”的赤子情怀熔铸骨髓。作为新时代青年,我们需承继“挽车不问荣辱”的纯粹,亦要锻造“方言即战壕”的智慧。青年之志既要深植云端理想,更须俯身触摸大地纹路,在新时代续写布衣赤心的壮阔史诗。
商韵声声,一起学习。让我们一起,聆听英雄故事,奏响奋进凯歌。

朗读者介绍
王晨悦,2024级专业工商管理5班优秀团员
朗读选段
我们来看陈延年吧——
这位当时年仅28岁的中共上海地区领导,之前接替周恩来任广东区委书记。
在广东,由于陈延年一开始不会讲广东话,接近工人和农民有些困难。于是他努力在语言上攻克难关,并积极投身到工人中去,经常与人力车夫一起躬着身子拉车。当时的香港《工商日报》为了诋毁共产党人,曾就此事发过新闻,讥笑共产党的干部当“车夫”。陈延年知道后,不仅没生气,反而非常高兴,他对身边的革命同志说,共产党人当车夫,这不是耻辱,而是十分光荣的事,因为我们是劳动人民的政党,这有什么不好呢?
他很快打开局面,在不到两年内,发展党员人数从过去的几百人,猛增到五千多人,仅此就很能说明陈延年的工作能力。
在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时,广东声援上海的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,是中国工人运动乃至国际工人运动中的辉煌篇章,而这正是陈延年与其他革命者一起领导的结果。
陈延年及弟弟陈乔年,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人生里,几乎没有沾过父亲的一点“荣光”,相反,伴随他们的常常是无尽的艰苦和一次次的危险……
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从小都在老家安徽安庆生活。1915年父亲从日本回国后,全家人才搬到上海,居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一幢砖木结构的小楼里。那个时候,陈独秀的生活并不好过,其妻高君曼患病严重,身边又有两个十来岁的儿子,最主要的是陈独秀很不“安分”,一心忙着办杂志,可又没钱,虽然有朋友帮忙,但全家生活仍十分艰难。这一年,由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横空出世,给中国革命带来无限光明,可对陈家来说,陈延年只能带着弟弟一边上学,一边打工以维持生计和交学费,常常处在饥饿状态,而且他们还要照顾有病的母亲。但即便如此,陈延年仍然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各类新书刊,包括父亲编的《新青年》。父亲陈独秀在家里也很有些家长式的霸道,儿子们既怕他,又有些恨他,但“老子”的文章却又被儿子偷偷地喜欢。比如《新青年》上的创刊词,“青年如初春,如朝阳,如百卉之萌动,如利刃之新发于硎,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”云云,陈延年读得热血沸腾。因为喜欢法文,陈延年的法文功底很好,于是在五四运动之后,留法勤工俭学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之时,陈延年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。陈独秀马上答应:“好啊,这个我非常支持!”正在帮助一批批青年干部去欧洲深造的陈独秀,对儿子的想法十分支持,并且在陈延年提出带弟弟一起去时他略深思了一下,便点点头:“也好,你们一起去、一起回,相互有个照应,留在我身边反而不是良策……”
于是,1920年初,陈延年带着弟弟陈乔年,加入了留法队伍,成为了蔡和森、赵世炎和周恩来等革命青年队伍中的一员。[1]
[1]节选自《革命者》
文字:施文、汪千睦
图片:汪千睦
音频剪辑:陶雪